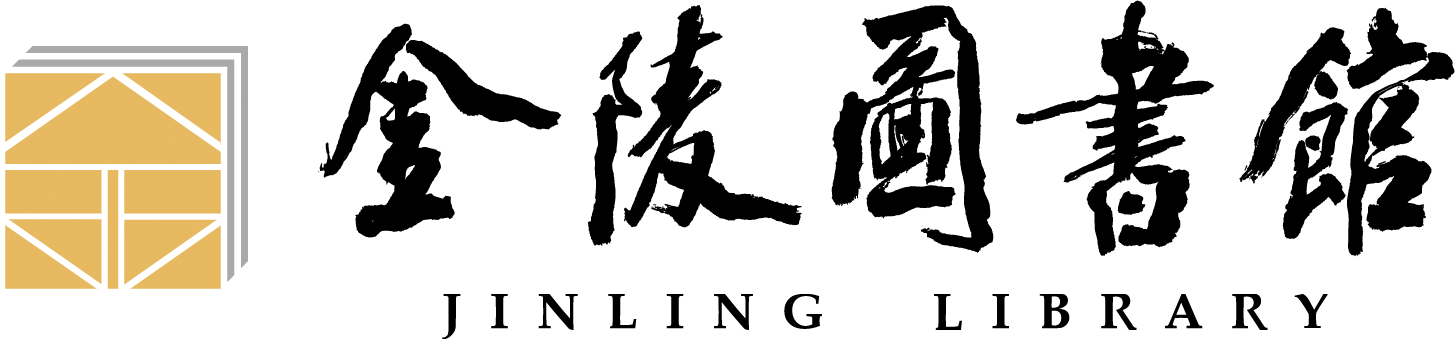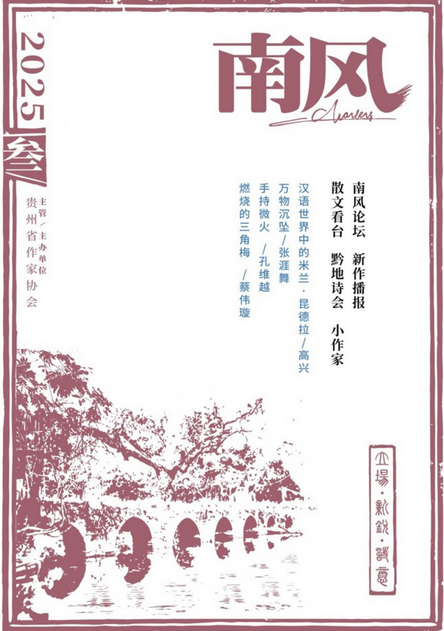
邹德斌
邹德斌:贵州桐梓人,现居桐梓。
一
焚尸工灰扑扑的眉毛抖了几抖,真叫人担心有灰尘抖落下来。其实不用担心,他就是抖下再多的灰,也掉不到老毕脸上。
老毕的脸上盖了一把大蒲扇。蒲扇把他的脸盖了个严严实实。焚尸工的眉毛又抖了几抖。自打火葬场建成以来,他就在这里焚烧尸体,他的眉毛从最初的黑荫荫,变成了现在的灰扑扑,他烧的骨灰都埋在火葬场背后的墓地里,那片墓地乌泱泱的从山脚一直蔓延到了山顶,差不多是小半个县城的规模了,可他还是第一次见到逝者的脸上盖着蒲扇的——他们绝大多数盖的都是黄裱纸,偶尔也有盖本书的,也有盖红头文件的,还有盖证书跟美元英镑的,这些都属于“正常”情况。逝者的脸上所盖的物件既是他毕生的追求,也是亲人和组织对他盖棺定论的历史性总结。但是眼下,异常稀奇了,冷灰堆里头爆出颗热豆来了,逝者的脸上盖的是一把大蒲扇,蒲葵做的,陈旧的大蒲扇。他就身份不明了。见多识广的焚尸工都有揭开蒲扇看一看的好奇心了,这样他就不由得抬头看了看窗口的孝子及其亲友们,这把蒲扇盖在这个逝者的脸上是那么的神秘,毫无由头,他想从他们的脸上找到由头。他搞不懂这里头到底有什么讲究,或者说这是最后的孝敬跟祭奠方式?
作为孝子,其实毕顺也搞不懂,毕顺琢磨了一辈子也没搞懂,毕顺不晓得他老汉为哪样要手不离扇,毕顺不敢问,毕顺他姐也不敢问,怕他老汉儿老毕拿扇把儿敲脑袋,敲出几个青包来。好在我们豆芽街的街坊敢,他们有人问过老毕,他摇着那把大蒲扇,万变不离其宗,“一把扇子半把伞,还顶半个草帽哪。”这话听上去很是理由,但又等于啥也没说。问毕顺妈,她说,“嫁给他以前就这样了。”声音轻得像蒲扇扇过来的风。她这辈子嫁的就是那把蒲扇。
没人晓得老毕是啥时候养成这个习惯的。
几十年来,我们豆芽街的街坊都习惯了,一年四季,老毕扇不离手。是的,一年四季,春夏秋冬,三百六十五天。夏天倒也罢了,夏天握一把蒲扇是勉强说得过去的。说“勉强”是因为,整个夏天,从重庆来我们这个高原小县城避暑的游客也都用不上扇子,被称为全县“四大酸”的四个文化人,也没有一个手摇扇子的(当然了,他们要摇的话肯定也是折扇而不是大蒲扇),但是“一把扇子半把伞,还顶半个草帽哪”,一辈子靠赶乡场倒腾山货的老毕,夏天里用扇子是勉强说得过去的——负重行走在山路上难免出汗,再说用蒲扇挡挡日头跟突然而至的山雨山风也说得过去。春天秋天呢,也勉强说得过去,老毕爱喝点小酒,喝了酒身子也难免燥热,用扇子扇扇风降降温也算正常。但是,冬天,冬天也手握蒲扇,怎么解释,没法解释的,怎么解释也通不过的。我们全县本就是高寒山区,冬天时日更长,刚一立冬就冰天雪地了,呵气成冰了,白日夜晚小北风刀子似的割耳朵,谁都恨不得把脑袋缩进肚子里,老毕却戴着棉手套,顶着大棉帽,老棉鞋上还绑着两个草脚马——家里屋外,进进出出,摇一把大蒲扇,雪上加霜啊。这个就烧包了。
盖在老毕脸上的那把大蒲扇已经很陈旧了。蒲扇用食指宽的鸡肠带绞了边。当初的鸡肠带跟蒲葵一样,乳白色,现在,它们都成了一体的褐黄,匀实的针脚还若隐若现在褐黄里。扇把儿也用鸡肠带缠了好多层。把儿头上,烙了个孔,穿了尼龙绳,结成套,老毕不握的时候,手腕就让套子套着,走起路来,扇子一甩一甩的。
现在,毕顺不能让老汉儿跟他的蒲扇分开,情感上过不去,也没有分开的必要。毕顺晓得,这也是他老汉儿最后的愿望。
焚尸工抬起眉毛看了看窗口的毕顺,毕顺还盯着那把蒲扇。焚尸工终于咽下了他的好奇,把蒲扇和老毕轻轻送进了火化炉,轻轻关上了炉门,轻轻按下了按钮。轰,那把蒲扇跟随老毕一同在烈焰中燃烧,老毕和它融为一体,不分彼此。如果老毕和蒲扇之间真有什么秘密的话,现在也全化成灰了。
等待焚化的过程中,毕顺反倒有一种轻松感,仿佛也放下了那个探究了几十年而未得的秘密。
二
老毕手握一把蒲扇的形象成了毕顺的软肋,同学们都给他取绰号了,他们叫他老蒲,或者老扇。气得毕顺好多次都在半夜悄悄爬起来,要偷了那把蒲扇扔厕所里,可老毕扇不离手啊,哪怕半夜,哪怕睡着了。
同学们越来越肆无忌惮了,他们甚至怀疑道,扇哥,你老汉儿是不是拿蒲扇当道具,用它掩人耳目,好在乡场上偷东西。
他老汉儿是诸葛亮呀,那把扇子是要借东风的。
他借的哪里是东风,分明是跛子放的屁,一股邪气。
要是打起仗来,他会不会拿扇子当盾牌挡子弹呀?
你老汉儿是不是脑壳有问题哟?
老毕的脑壳没有问题,哪怕他喝醉了,脚下有问题,再宽的马路都不够走,脑壳也没问题,因为他从来没有丢过蒲扇。相反,他的脑壳比谁都清醒。问他那个问题,他就呵呵两声,一把扇子半把伞,还顶半个草帽哪。再扇几扇,就把你的疑惑跟好奇扇开去了。不是因为大家的嘲讽,老毕他才执拗的。也不是老毕的神经要比常人粗壮,从来都不在乎那些嘲讽。反正,他就是要握一把蒲扇在手上,好像天生的,娘胎里带来的。
有女人逗毕顺,你老汉儿洗澡的时候,扇子是不是挂在他的水龙头上面呀?
毕顺说,我不晓得。我又没跟他洗过澡。
她们又问,你老汉儿睡觉是不是也用扇子盖在脸上呀。毕顺说是。这个毕顺白天晚上都偷偷见过,老毕的鼾声还吹得扇子一扑一扑的呢。她们又问,你老汉儿跟你妈晚上打架的时候是不是也拿着扇子呀?毕顺说不晓得,我没见他们打过架。她们哈哈大笑,又嬉嬉地说,蒲扇里头肯定藏着啥宝贝,说不定是他的命根子。
毕顺和他姐也怀疑过,老汉儿会不会把存折藏在扇把儿里?很快他姐自已先否定了,说,又是汗又是水的,还不捏碎了?而且她亲眼见过母亲给新蒲扇绞边儿,没有的事,扇把儿就缠了几圈鸡肠带。毕顺说是咯,那些旧蒲扇他都连着鸡肠带丢灶膛生火烧水了。
确实是再普通不过的一把蒲扇。
因为蒲葵薄而脆,蒲扇容易破损,何况有时候老毕还要拿它当座垫,有时候买点小东小西,人家卖家没袋子了,他还得用蒲扇兜兜,也难免要磕磕碰碰。这样说来,并不是说老毕不爱惜他的蒲扇,但他也没有把它当成心肝幺儿似的呵着护着稀罕着。就像一个穷人家的父亲对待自己孩子的态度,粗心,哪家的孩子不是摔大的?蒲扇破了,老毕就用胶布在两面对粘一下,实在太破了,才在赶场的时候,从乡下砍了蒲葵回来,剪成扇形,阴干,扇把儿的棱角也拿刀削刮平整了。扇边儿有毛刺,他就让毕顺妈用食指宽的鸡肠带绞上一圈。毕顺妈手巧,绞的针脚跟小脚女人的步子似的,细而匀,小心翼翼,生怕迈大了,迈歪了,落人笑话。扇把儿也让鸡肠带缠了,不硌手。把儿头再烙了小孔,穿上尼龙绳,结成了个套环。一把蒲扇简朴又实用。
有时候没有买到合适的土货,老毕也会砍几枝蒲葵回来,拿旧扇当模子,比画着剪出大致的模样后,把它们码在檐下阴干,再让妻子绞了边儿,缠了把儿,做成蒲扇,送给街坊邻里。毕顺姐稍大了,敢怼她老汉儿了,老汉儿,你干脆做蒲扇生意嘛!老毕认真道,能卖几个钱?送给他们只是拿来赶蚊虫苍蝇。老毕看得清楚,不说我们豆芽街,放眼整个县城,除了他自己,没见一个人手握蒲扇的,哪怕大夏天。毕顺他姐说,等我出嫁时,你就送把蒲扇给我作嫁妆。老毕听出了这话里头的骨剌,横眉竖眼地瞪她两眼,要不是看她是个大姑娘了,脑门顶肯定要被扇把儿敲起青包来。
毕顺不敢劝老汉儿,别大冬天的握把扇子扇,太现眼了,太臊皮了,就像是故意现宝气。毕顺在同学那里受了羞辱也不敢回来跟老汉儿叫屈,他不会听你申述的,他只会拿扇把儿敲你的脑瓜子,哪怕缠了鸡肠带,也敲得你生痛,眼前金蛾子乱飞,青包好久不散,又得让同学嘲笑。毕顺只敢跟他妈使气,叫老汉儿别拿把扇子出去现眼啊!可他妈也不敢在老毕面前多嘴。这个家,他妈从没当过家,甚至连个态也没表过,哪怕每顿煮干煮稀,都老毕一锤定音。他妈只负责陪笑跟抓落实。
毕顺姐时不时地嘀咕,哪哪都臭,都苍蝇蚊子,就他讲究,得扇一扇。
毕顺心里老大不痛快,怼他姐,冬天哪来苍蝇蚊子。毕顺恨那把蒲扇,那把蒲扇绑架了他的童年。直到后来很久了,毕顺有时候还恨恨地想,贼不走空!
蒲扇是老毕的另一只手,哪怕一时半会不用,也片刻不能离开。离了人就残了,就不是个圆全的人了似的。
老毕喜欢喝酒,偶尔兴致到了也喜欢进厨房,洗菜烧菜时,手腕子上也没离开过那把蒲扇,毕顺姐弟俩看了都嫌碍事,他却一点也没觉得。老毕有一绝活,做菜不尝,蒸煎炸炒,凉拌水煮红烧,腕上一抖,扇把儿握到手上,往面前轻轻扇两下,火候,咸淡,鲜香,只闻扇过来的风就判定了。他可真是香也扇,臭也扇,热也扇,冷也扇。
老汉儿是带着蒲扇生下来的吧?有时候毕顺夸张地想,扇子更像根拴牛桩,一直拴着老汉儿,只不过是一个移动的拴牛桩。或者也像一副手铐。
好在,千恩万谢,老毕他没有要求毕顺和毕顺后来的儿子臭臭跟他一样,啥时候手里都握一把蒲扇。那样的话不如去死。好在没有。一辈不管二辈事吧?儿孙自有儿孙福吧?毕顺姐呢,早迟泼出去的水吧?老汉儿他没有要求。谢主隆恩。
三
毕顺打记事起,就见老汉儿手上握了一把大蒲扇,那把蒲扇就再没离开过他。
不对,准确地说,其实,那把蒲扇也不时离开老汉儿的双手。想到这里,毕顺眼前就会出现那条雪花纷飞的山路。
毕顺印象深刻的那个寒假,挨近春节的那天,老毕叫毕顺跟他去赶乡场,置年货,一路上,毕顺对他老汉儿那把蒲扇有了复杂的认识。
那天的场脚不远也不近,一个单程接近二十里。天不见亮,老毕就背着背篼,摇着他那把大蒲扇,一头扎进了飞雪里。毕顺也背着背篼,戴着耷耳帽在他身后紧追慢赶也赶不上。出了城,老毕缓下了步子,等毕顺走近了,他把手上那把蒲扇递给他,哈着雾气说,拿去,遮挡遮挡。毕顺没接,毕顺把耷耳帽扣得更紧,压得更低,眯着两眼超过了他老汉儿。老毕在他身后嘀咕道,别人的屋檐再大,都不如自己有把蒲扇。
老毕横着蒲扇,在额头前半尺开外,借它遮挡风雪,风就吹不到他的眼睛里,雪也钻不进他的嗓子跟鼻孔里。
毕顺心里老不爽快,县城早就有班车通到乡场了,老毕不坐车,说要“走两步”。这是走“两步”?不就是图省几个钱。
终于到了乡场,老毕要了两碗羊肉粉,他右手挑粉,左手握扇,不停地扇,滚烫的羊肉粉很快凉下来。老毕呼呼有声,三下五除二,几口把汤都喝尽了,侧过头看毕顺,还有大半碗。老毕又用扇子扇他的满头大汗,边扇边不屑地乜毕顺,“狗肚子里存不下二两酱油,你这么斯文,要是赶在那些年只有饿死。”毕顺更不屑,在心里怼他,哼,带上这把蒲扇就是为了抢食!
毕顺发现,不光乡场上的行商坐贾,就是一路上那些农家的狗都认识他老汉儿的蒲扇,它们远远地冲他摇尾巴,连尾巴根都在摇,老汉儿也冲它们摇蒲扇,叫着它们的名字打招呼。
年货是个大篇目,只要到了乡场,见到合适的都可以买,老毕晓得带回县城去的差价,实在卖不完了,才留成自家的年货。猪头猪蹄,干辣椒大蒜土豆片,都可以上手。老毕不时把大蒲扇从左手换到右手,又从右手换到左手,有时过秤,他就把蒲扇插在后腰皮带里,腾出两手来。
返程路上,天空中仍下着大雪,老毕他又把那把蒲扇插在后颈脖,给毕顺和他自己的棉鞋上绑了两个草脚马。风从身后刮来,他后颈脖里插着的蒲扇像船撑起的帆,他既借助风力走得轻快些,又可以挡住那些风往脖子里钻,往耳朵根割。毕顺在后面看到大雪里的天光照射过来,他老汉儿的影子投到地上,是一个巨大的脑袋。
累了,父子俩翻过岗坡,就寻个背风的林子歇下来。老毕把蒲扇垫在雪地上,让毕顺坐,他自己则坐在背篼上。等他们歇得差不多了,再起身时,他又用蒲扇拍打毕顺屁股上的残雪。
此后,毕顺也不时见到过蒲扇类似的离开老汉儿的双手,双手总有不空的时候,提水提煤啦,捧柴抱菜啦,老毕就把扇子插在后腰上,或后颈脖里。但更多的时候还是握在手上,或套在腕上,不是左手,就是右手。
四
不像身上痒痒了,会不自觉地伸手挠挠,老毕的手握蒲扇没有理由,尤其大冬天的,任何理由都不是理由——只能解释为类似植物神经系统的本能反应了吧?时不时扇两下,不急不缓。风度是没有的,这样一把蒲扇跟风度无关,也跟温度无关,就是没有任何理由,不需要任何理由。世间好多事情大多如此,没有理由就是最大的理由。正如不是所有的所以都有因为,哪怕是个一辈子了的所以。如果真要找个理由的话,那就是“一把扇子半把伞,还顶半个草帽哪。”倒是童言无忌,那天看着电视,臭臭突然说,爷爷,你是济公啊!惹得老毕难得地哈哈大笑,拿扇子敲了敲臭臭的脑袋,不是扇把儿。说,对,这是你爷爷的护身符。臭臭去抓他的扇子,说我也要当济公。老毕不让,说,爷爷给你做一把。
老毕还真来了兴致,他当真送了一把蒲扇给臭臭,比他那把小了两圈。来,臭臭,拿去当济公。臭臭接过扇子很开心,学着电视里的济公,一边摇着蒲扇,一边唱起了鞋儿破,帽儿破。叫毕顺哭笑不得。
拿着蒲扇,臭臭在街巷里到处挥舞,舞得灰尘四起,成了个花猫。但很快,臭臭对蒲扇没了兴致。啥时候扇子不知所终了,老毕也没有过问,仿佛不曾发生,只要他自己手上那把蒲扇没丢就行。
那把蒲扇要是与一根旱烟杆,或一根拐杖相组合,就标配了,就协调了。毕顺无数次这样想。可老毕不抽烟,不需要旱烟杆,老毕腿脚还利索,也不需要拐杖。其实,他应该最不需要的正是那把蒲扇。毕顺固执地想。
你拿根拐杖,拿根烟杆,或者拿把伞——饱带干粮晴带雨伞嘛,毕顺都能理解,也都跟你这个赶乡场的小贩相协调。蒲扇?特别是大冬天,别扭啊,不着四六啊!毕顺和毕顺姐替他着急,臊皮。
为此,早年间两姐弟老是想,蒲扇里头肯定有故事,或者事故,或者秘密。不光姐弟俩这样想,毕顺妈,还有我们豆芽街的街坊,都这样想。只是,谁也不晓得真相。一年四季从没离手的大蒲扇,里头没有秘密才怪呢!可你就是想破脑袋也破解不了那个秘密。好多时候,连毕顺妈都想糊涂了,真有秘密?人家探秘好奇的街坊问起,她只嘿嘿地笑,说,路边林子里解个手,用来遮挡遮挡,用来赶山蚊子咬屁股,散臭味儿嘛。
一个长年跑乡场的小贩,他手上那把破蒲扇,能有啥秘密?
没有秘密他又为哪样从不离手?矛盾哈?矛盾大了哈?
最想破解秘密的,当然是作为儿子的毕顺,他是最大的“受害者”。毕顺绞尽脑汁,想到了一个儿童和少年所能想到的各种可能,他甚至想到他老汉儿会不会是“那边”派来的特务,那把蒲扇会不会是一个特务跟另一个特务接头的暗号。我们整个豆芽街都在猜想,毕顺娘刚嫁过来那两年也在猜想,最后都想不明白,不了了之。
总之,各种猜想,到底只是猜想,到底均告失败。老毕手上那把轻飘飘的蒲扇,强大地战胜了豆芽街的全体街坊跟几十年时光,蒲扇轻摇,谈笑间,樯橹灰飞烟灭。再后来,我们就见怪不怪了,就“正常”了,再正常不过了,哪天老毕他要是没有握着这么一把老蒲扇才是不正常呢。但这样的事故从来没有发生过,哪怕半年前,老毕他住进了医院,两只手腕上的留置针轮换着扎,他也没有丢下他的蒲扇。
五
得知老汉儿生病了,毕顺从省城匆匆往回赶。在候车厅,毕顺看到一个卖文创产品的柜台里有檀香的折扇,有锦缎的团扇,也有篾片编织的类似于蒲扇造型的扇子。毕顺咬牙买了那把篾扇,回来给病床上的老汉儿轻轻扇着。正是夏天,病房里也有空调,毕顺还是替老汉儿轻轻扇着,微风徐徐,篾扇比蒲扇好看,又轻便结实,金黄剔透的,看着都清爽。老毕却看都没有看那把篾扇一眼,他闭着眼,摇着蒲扇,埋怨道,钱多得花不完了。
爬满老年斑的手背,干瘦的五指,握着蒲扇,缓缓摇着,有看不见的风拂过。毕顺一时想,老汉儿他握的分明是胜券,是江山。
毕顺恍惚有些懂了,是蒲扇在握着老汉儿。蒲扇才是老汉儿的主人,老汉儿只是蒲扇的仆人。就像一块土地,你以为你是它的主人,可一年四季你却得伺候着它,营管着它,躬腰驼背地挥洒苦汗,分明是土地的仆人。老汉儿他是为这把蒲扇活着的。蒲扇让他活得镇定,沉实。就跟有的老人要拄拐杖,拄烟杆一样,这样才能保持身体的平稳,这样才能让心里踏实。
病床上的老毕轻轻摇着老蒲扇,蒲扇扇开了挡在眼前的东西,是看不见却又仿佛确实存在的挡在他眼前的东西。扇开了,可是呢,又感觉是让那把蒲扇挡住了,遮掩了。
毕顺不晓得自己到底懂没懂得老汉儿和他手上那把蒲扇。
那天,病床上的老毕刚换了留置针,臭臭一边喂他吃无花果,一边建议他把扇子从手腕上取下来,他不,他告诉臭臭,爹妈给你一双空手来,你最后也得空着两手去,但你是个活人,你活着的时候手上就不该空,好歹总得拿着点啥。他平静地说着车轱辘话,拿着点啥,心才稳。
啥时候都拿一把蒲扇,哪还腾得出手去拿别的啥?臭臭问爷爷,我们不能让一把蒲扇就把手给占了吧?臭臭也早就看不惯爷爷手里那把蒲扇了。
老毕品味着无花果,很是满足的神情,说,各人的手上有各人的抓拿。
老汉儿的手上抓拿一把蒲扇就知足了,蒲扇那么大一块天地能给他遮风挡雨,衣食饱暖,就知足了,就再不需要去抓拿别的什么了?
毕顺脑子一宕,这就是这个一辈子跑乡场的小贩,这个市井俗人,街头凡夫,跟他那把蒲扇的全部秘密?
当天晚上,老毕去世了。我们不能断定他去世的准确时间,因为,一夜里他都用那把蒲扇盖在脸上,这是他一辈子的习惯,当毕顺发现那蒲扇没有了哪怕轻微的一扑一扑了,再唤他也不应时,揭开蒲扇,他面色安详,不知几时已停止了呼吸。
现在,老毕的骨灰装进了黑色的大理石骨灰盒里,看上去显得特别沉重,也特别沉默。骨灰盒要送进墓穴里。从焚尸场过去,有一段二十来分钟的路程,主要是那段一眼望不到山顶的石梯,石梯上铺着厚厚的积雪,很让人心生畏难。天空中雪花飞舞。毕顺又从包里拿出一把崭新的用鸡肠带绞了边的蒲扇盖在骨灰盒上,在我们诧异的目光中,捧着骨灰盒,送往墓地。有雪花飘落在蒲扇上,转眼化成水渍。
骨灰盒上盖了蒲扇,就是一个懂得老汉儿的儿子了?
我真懂了?毕顺看着胸前的骨灰盒,一路上想,这个一年四季,春夏秋冬,三百六十五天,哪怕吃饭睡觉拉屎拉尿,都大蒲扇不离手的世上最亲的亲人,我真的懂了他?毕顺恍惚感觉,正是那把蒲扇挡在了他们父子之间,让他看不真切,没法搞懂他的老汉儿。
但毕顺好像又是懂一点老汉儿的。不然,毕顺不会用那把蒲扇为他盖脸,陪他一并火化。不然,毕顺不会用这把蒲扇盖在老汉儿的骨灰盒上。可这种懂又真是模糊的。因为模糊,反倒有了囫囵敷衍的性质。毕顺姐悄声问他,今后逢年过节,我们给老汉儿上坟,也烧蒲扇?毕顺没有点头,也没有摇头。
雪,无声下着。积雪让石梯有了些微弹性,有了不真实感,踩在上面,噗哧噗哧的声响仿佛来自地心深处。终于爬上了山顶,这是公墓离天最近的地方。毕顺将骨灰盒轻轻推进墓室,合上墓门。现在,老汉儿和他的蒲扇都成了灰了,入了土了。如果他与蒲扇有什么秘密的话,也都永远地消失在地下了。但毕顺更愿意相信,一辈子就靠跑乡场养活一家人的老汉儿和他那把蒲扇,根本就没有什么秘密。是的,我们的生活并不存在一条故事发展的因果链。老汉儿跟他的那把蒲扇之间没有秘密,没有故事,没有事故,没有情节和矛盾冲突。这一切都是旁人强加给老汉儿的——这就是真相。毕顺莫名地想到那天臭臭喂着爷爷吃的无花果,其实因就在果里,果就在因里,其实众多的因与果是互为一体的,就像老汉儿与蒲扇的俱已成灰,不分彼此。仅此而已,如此而已。
公墓统一种植了柏树,两人高大的塔型树身堆满积雪。毕顺决定,要在老汉儿的坟墓两侧再移植两棵蒲葵。就像毕顺不懂老汉儿为什么一辈子手不离扇一样,现在,他也不晓得自己为哪样想要移植两棵蒲葵。或许,这里头有着某种情感的或是精神的移植?他没有来得及细想就蓦地打了个寒颤,他惊骇地发现,他的左手腕上套了一把崭新的蒲扇,正是刚才盖在骨灰盒上那把,它却好像天生地就长在他的手上。毕顺竟然握着扇把儿了,竟然缓缓地扇了起来,不急不躁的,稳操胜券的。这是雪花飞舞的腊月哪,正是那年跟老汉儿去赶乡场置年货的腊月哪!飞雪迷眼,毕顺一时分不清这个摇着蒲扇的人是现在的自己,还是当年的老汉儿,或是未来的臭臭。更让他惊骇的是,两手吞在袖筒里,脖子缩在胸腔里的街坊们,竟然一点也没有流露出惊骇的神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