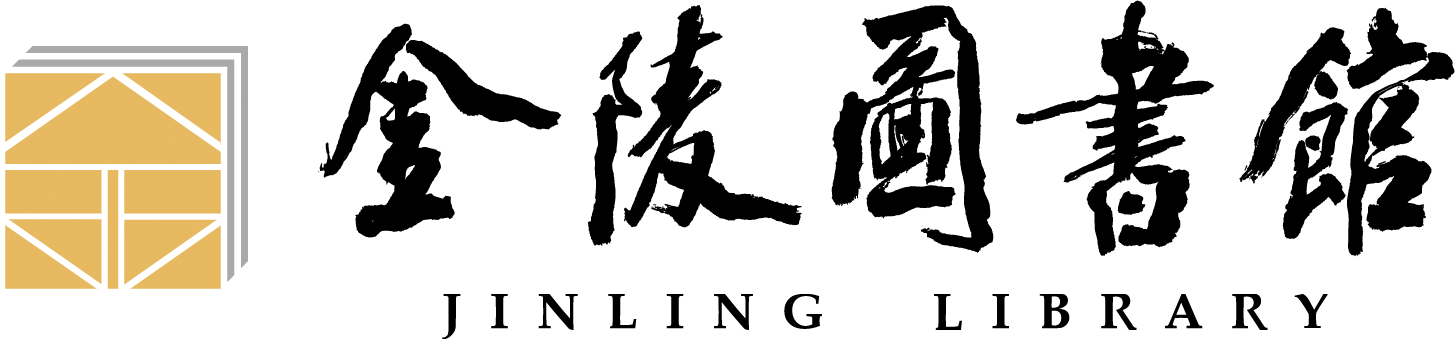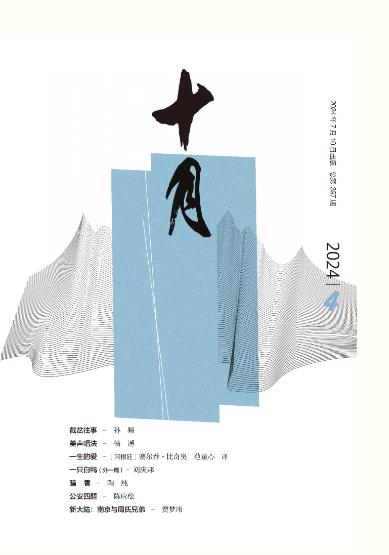
喜欢“桑”。《诗经》里有“无折我树桑”,《穆天子传》里有“天子命桑”,《古乐府》里有《陌上桑》,孟浩然诗里有“把酒话桑麻”。桑,弥漫着古典中国山水田园的气息。
松古盆地就像一片桑叶。四围连绵的群山似边缘卷起,主脉是松阴溪,依主脉错生开来的三十余条支流是它的叶脉。那些更细小的筋脉之间构成了一块块几何图形,田园与村居。松阳以其中的二十六条支流分成二十六个辖域,称为“一都源”“二都源”“三都源”“四都源”,依次到“二十六都源”。“源”做后缀,读出了一种水乳交融的情感。
在松阳水利博物馆绘制的这片“桑叶”前,伫立良久。在一个小时前,我就从这片桑叶的主脉底部,也是松阴溪的入江口,逆流而上。确切地说,我是从瓯江的下游而来。此次于我是溯源之行,也是一次逐水之旅。
逐水是人类的本性,也由此创造了灿烂的人类文明。松阳的先民沿松阴溪而来,居住在松阴溪畔的小山坡与盆地上。先民们在松古平原上拦起了第一道水坝,种下第一粒种子,当然也渔猎,也采集。遗留下来的石镞、石斧、陶罐、瓷豆,过去了四千多年依然散发出光芒。
两千年前,东瓯先民北迁江淮走得也是我今天的路线。汉武帝建元三年(前138),东瓯遭闽越围攻,遂向武帝求救。闽越撤兵远去后,“东瓯请举国徙中国,万悉举众来,处江淮之间”。汉武帝将东瓯国民安置于江淮流域的庐江郡,就是今天安徽省舒城一带。东瓯王率领部属军队四万余人北上,从东瓯国都城所在地温州,走水路途经松阴溪畔的古市,见平原灌溉条件优越,部分军民便留下开垦耕作,补给北迁军民的粮食。一些眷恋故土避至山区的越人回迁,在松古平原上定居下来。汉献帝建安四年(199),松阳置县,治在古市,是处州(今丽水市)最早的建制县。在这样的暮春时节,先民们在松古盆地的“子规声”里,“采了蚕桑又插田”的耕作情景可想而知。
南方的迁徙,对应着战乱的灾难——衣冠南渡,安史之乱,靖康之难,北方士与民不断地朝着浙西南这片山野走来,沿着松阴溪以及三十余条支流选择并开发各自的生活场域,形成了一百多个村落——雅溪、力溪、樟溪、桐溪、陈家铺、杨家堂、松庄、酉田、南岱……蛮荒的山野染上层层烟火。一千八百多年的时光过去了,重重山峦将时间屏蔽,他们还是把炊烟袅袅升起。
沿着“三都源”走,山深林密,涧水曲折,仿佛到了尽头,才见有村人在路边售卖山货。古木遮天,村口狭窄。由山道辗转而入,才见村居错落在峡谷激流一段和缓处。村名松庄。溪上有一座单孔石拱桥,如明月步虚,空灵飘逸。小溪,古桥,碇步,堰坝,梯田,民居,相生相融,恍若武陵桃源。山中的小桥流水人家,不饰雕琢,古朴典雅。
宋水秀仿佛就坐在桥头等我似的。我们坐在一起闲谈。七十三岁的她,五十多年前嫁到松庄,夫家有四个兄弟和四个妹妹,她嫁的是老三李文生,儿子在松阳县城工作,女儿远嫁金华。听着哗哗的水声,想象年轻时的宋水秀,就在溪边用白嫩的手洗衣服,坐在桥头奶孩子……“宋水秀”作为小说或剧本里的女主角,可好?
膳垄村在“十九都源”,村子像一叶小舟泊在一片狭长的山谷坡地上。村旁涧水飞落成瀑,落入深潭,满溢出来,穿村而过。一户人家门上的春联这样写——“屋后青山步步春,门前绿水声声笑”。周仕方的家门朝着溪流而开,老人家正在做谷耙。秋天里用到的农具,春天就开始准备了。
不知谁说过,人类所有的智慧都在流水所经之处。山里的水奔入松阴溪,浩荡地流过松古盆地。松阳人称松阴溪为母亲河。还有什么能比这三个字更好地表达出对一条江流的认识吗?
2
逐水人,也是治水人。他们逐水而居,也治水而兴。
松古盆地,自古就是“处州粮仓”。当地有民谚说“松阳熟,处州足”。松阴溪上的一百多座古堰——金梁堰、白龙堰、青龙堰、午羊堰、神坛堰……堰堰如龙,感应着天时、地利与人和,关系着千家万户的烟火人生。
沿着松阴溪走,去看古堰。
暮春时节,冷暖交替,时雨时晴,远山远水隐在薄雾里。天地间的绿色,让松阴溪消融了源源不断地送过来。松阴溪的绿,是豆绿,不是青绿,青中有蓝,还是闷着了,看看龙泉青瓷的釉色,就知道了松阴溪的水色了。
大溪上那道白花花的,就是白龙堰。以白龙之名,是人们祈望神力能护佑这条堰坝不被洪水摧毁。白龙堰始建于元末,是里人周汉杰捐资并鸠工筑成。
修筑白龙堰时,是在冬天。乡民们将毛竹分瓢剖成几绺,根部留着,编成竹笼,再将溪中卵石填入竹笼,然后将一个个竹笼堆积成坝。这样的智慧,来自民间的经验积累。竹笼装卵石砌坝,是宋元时期的堰坝坡岸砌筑法。明万历十六年(1588),松阳知县廖性改为砌石堰,又几度被洪水冲毁重修。现在的白龙堰,是浆砌块石堰。白龙堰引出的圳渠,全线长达四千余米,惠及了堰渠两岸项弄与白沙等村的两千多民众。
离白龙堰不远的北岸,有一座石柱殿依山面溪,是当地乡民感念周汉杰的治水功德而建。墙上绘有周公平山寇保乡民、明师入境守御处州、捐资修建白龙堰等事迹。从白龙堰引来的渠水缓缓从殿前流过,一棵苦楝树守在殿旁,花开得如云似霞,香气浮动,随风传远。
春江水阔,独山似金蟾出水,领山水之风骚。此山也叫百仞山,旧筑有“百仞堰”。明万历二十三年(1595),作家、戏曲家屠隆应松阳县令邀周宗邠到松阳采风,留有《百仞堰记》。文中开篇就记叙了明正德年间,百仞堰坏,然一直未恢复。明万历二十二年(1594),周宗邠甫一上任就遭遇百姓上访,恳请修堰。七十余载过去了,两岸农田荒芜已久,多任县令为什么不修复?水利是民生工程,是一方父母官分内的事,无论多难,周宗邠决心予以解决。
周宗邠多次去实地踏勘水脉,终于找到了症结所在:原堰址在四都源下,如果筑堰,南岸虽可灌溉,但北岸乡民就会发生内涝,因此南北两地乡民一直争吵不休,筑堰之事一直悬而未决。
周宗邠有何良策?他将百仞堰坝址向西上移了数百米,新坝址地势稍高,南面可解决灌溉,北面又不会发生内涝之患,既可收水之利,又可绝水患,南北两地都周全了。
屠隆在文中总结了周宗邠的治水经验:成功难哉!在权利害。利七害三则兴利;利三害七则避害,利害相半,与其有利,不若无害。“三七原则”,是历史上首次出现的水利工程兴建与否的定量分析原则。
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,在堰旁立“周侯治水德碑”,记其功德。
百仞堰也称青龙堰。明万历二十六年(1598)改为砌石堰。在这源远流长的松阴溪上,建坝保民生的周宗邠不是第一个,也不是最后一个。现在的堰为砼连拱坝和重力坝,圳渠长七千米,灌溉着两岸的万亩良田。
水声哗哗,似有谈笑声,应是周宗邠带着屠隆、汤显祖他们在此观赏松阳的水利工程。山县寂寞,宗邠兄做此等利民之事功在千秋啊。长溪浩荡,青色的堰坝,如苍鹰打开翅膀,欲腾空而起。
3
芳溪,是一条芳草鲜美的溪流。
我首次见到“芳溪”是在松阳水利博物馆,它是“桑叶”上的一条支脉,在二十六都源里排第十三位。芳溪引起我关注,是因为存世的十九道水利榜文里,有十八道榜文关于“芳溪堰”。时间从明嘉靖九年(1530)延续到清光绪九年(1883)四月,内容涉及堰首、圳长、筹资、水权、圳图等,从中可以理出一张完善的水利管理系统图,还可以看到当时农村因水而生的社会状况。举例在此:
康熙元年(1662),榜文记载,知县批示,堰长照依旧例修筑古堰,并明确筹资、出工方案。
康熙二十五年(1686)六月初七,榜文记载,古榜圳图遗失,十三都芳溪源口、十四都肖周等村分水灌溉。
康熙二十五年六月十七,榜文记载,自宋朝以来芳溪堰的轮灌方案,即明确了堰坝水权由力溪、源口、五小坦获得。
康熙二十七年(1688)六月,榜文记载,时任县令认为前任县令制定的力溪灌溉六日,再五小坦三日,末源口五日的轮灌方案有失公允。重新调查有效灌溉面积后,对水权进行了变更。
康熙三十一年(1692)七月初三,榜文记载,芳溪二堰为源口、力溪、岗坞祖民所建,该三个村拥有芳溪二堰的水权。
乾隆十七年(1752),榜文记载,松阳县正堂黄槐为十三都下源口等四庄派定期任命圳长告示。
明清时期,松古灌区已普遍推行“堰董会”“圳董会”,其中的堰长、圳长,并不是个人,而是一个管理集体,有七至八人,类似于现今的董事会制度,其主要职责是负责堰渠工程的维修养护,日常用水秩序的维持,摊派民工、收取水费等维养经费的筹集。有诸多榜文及石刻为证,例如明嘉靖九年的榜文落款:“堰首:孙闵璋、周延庆、周明理、周□、周□福、周□□、周全、周□、周□。”县宪批复:“仰堰长会同该图里,克照田均贴工食修筑,毋违。执照。”
从榜文里可见,水权以投资为原则,谁投资,谁受益,但水权的获取、变更、交易、保障,皆由政府主导。圳图、水期榜文、水期勒石永示碑都是对水权持有的合法依据凭证,需要经过时任官府的批准并发布告示后方可生效。水权变更、调整等亦由时任官府颁布告示进行变更。
芳溪堰的十八道榜文,呈现了明清时期松古灌区完善的水利管理机制。芳溪堰因水权变更而发生的一件水利纠纷案件,其时间跨度之长,事件之反复,看得人惊心动魄。
自宋以来,芳溪堰一直推行力溪六天,源口五天,五小坦片区三天的十四天轮灌制。康熙二十五年古榜圳图(轮灌依据)遭洪水毁失,五小坦片区因田多水少提出变更水期诉求。康熙二十七年知县李钟秀判许变更,将源口、五小坦片区水期互换。康熙二十九年(1690),处州知府批查撤销县府变更,维持原轮灌水期。道光四年(1824),田多水少的五小坦灌片村庄的李某为了争取更多的灌溉水期,控告力溪村周某霸占芳溪堰水,并上诉至浙江布政使司和闽浙总督。时任松阳知县江思睿奉浙江布政使和闽浙总督批示审理此案,采取了力溪、源口不变、五小坦片区加一天的方案,将十四天一轮变十五天一轮。
芳溪堰的这个“十四日”与“十五日”的水权纷争,并没有因省府判定而结束。光绪七年十二月的榜文记载,时任县令郑县令依据史实及现实情况,变更有史以来的“十四日”轮灌方案为“十五日”轮灌方案。光绪九年四月的榜文记载,将前任县令判定的“十五日”轮灌方案勒碑永示,告示灌区群众不得再紊乱混争。之后,再无榜文记载这件事,应该平息了。
在松阳水利博物馆看见一张清光绪七年(1881)古圳图,绘制了芳溪二堰的水脉走向,上面标注了山塘、水碓、村庄的位置,特别多的是“演”(涵洞口),达四十多处,整个水利工程如长藤结瓜,水之利用,一目了然。
现在的芳溪堰已改为浆砌堰坝,铺了花岗岩的碇步。整个溪床被挖开一道深深的壕沟,正在兴修水利工程。溪岸立着一个铁皮告示牌,这是新时代的水利榜文,上面写着:
芳溪一堰始建无考,北宋即已存在,位于新兴镇下源口村十三都源上。2022年对引水闸进行提升改造。现堰坝长58米,引水干渠长2500米。工程受益村为下源口村、上安村、潘连村,受益人口5000人,灌溉农田3000亩。渠道用水计量设施采用水位尺,用水定额:200米3/亩,用水总量控制目标:37万米3,农业水价:0.215元/米3。
堰坝水闸管理单位:芳溪一堰水管会
责任人:刘金法 联系电话:138××××××××
松阳县新兴镇下源口村村民委员会
下源口村掩映在溪岸的绿树丛中,对面是田野,芳溪从中穿过。两位头发斑白的村人,正在堰坝上洗涤农具。曾经的水利纷争早已烟消云散,芳溪两岸人家的日子依然跟这条溪流相依相守。
4
从高处俯瞰松古平原——松阴溪贴着大地蜿蜒而来,沿途田园铺绿,民居累累,一条江流的化衍之力,以人类逐水而居的情状呈现眼前,如果用一个大词来表达,只有“伟大”。
松阴溪上的堰坝,引出圳渠,圳渠又生出更细的毛渠,还有蓄水的山塘和水井,把水脉源源不断地送达到每一寸土地。可以说,这里的每一片叶子,每一朵花,每一粒稻谷,每一个人,都是一条行走的松阴溪。
在松阳行走,你在遇见的事物上,都能感觉到这条江流的存在,感受到水脉的搏动,这是很美妙的感觉。特别是在南直街行走。
南直街,这条松阴溪载来的繁华街市,呈“丁”字形,把自己钉在明清时光里。明清是传统与现代的临界点。南直街对现代进程采取了断然拒绝的态度。
脚步前行,时光却在倒流——炒茶,裁缝,弹棉花,穿蓑衣,打棕垫,做竹椅,刻木雕,做马口铁,做秤,还有出售竹笋、苎麻糕、酥饼,甚至菜苗,一家店挨着一家店,时光缓慢而丰富,回忆代替了思考。
南直街10号是“祖字打铁店”。老虎灶居中,老虎灶边卧着一只圆筒形的手风箱。小铁锤、大铁锤、铁夹、砧子、水桶等工具无序地放着。师傅匀速地拉动手风箱,将风送入老虎灶。风箱“呼哧呼哧”地吹鼓着,炉膛内的木炭火苗“呼呼”蹿起来又扑出去。师傅用铁钳夹住铁块送进炉膛,火红从黑色的内部渐渐浸透出来。左手握着铁钳,翻动着铁坯,铁坯慢慢变得通红,然后夹出来,放在砧上,右手拎起锤子,“叮叮当当”,反复锻打,铁坯慢慢成形。
——锄头,用于田地翻耕、锄草;田刨,用于水稻耘田;耙,用于水田起埂,或者松土;耖,用于平整水田;镰刀,用于收割稻谷与麦子;犁头、斧头、柴刀、菜刀……
“祖字打铁店”从清末开始创业,经过阙樟通、阙法法、阙炳跃祖孙三代接力传承,在一百多年的时光里,究竟打制出多少铁器,已不得而知。据调查,本世纪初,松阳县城还有二十多家打铁铺。有多少件铁器,翻开沟渠田野,收割了多少的稻谷?可以用数据给想象插上翅膀——松阳县有十六万亩耕地,1984年,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十二万吨,达到历史的顶峰。1990年,国务院授予松阳县“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”称号。这些铁器与先民们的石斧、石锛、石镞之间,存在着一个传承有序的松古盆地。打铁店,或者一把新月形的镰刀,可以作为松古盆地农耕文化的符号。
苎麻糕热气腾腾地端上来,一条条像水波,又似草绳,绿意盎然,仿佛也是松阴溪的化身。松阳人在漫长的时间里逐水而居的情状——细微而盛大,日常而复杂,依赖而抗争。松阳,也成了人类逐水而居,治水而兴,理水而荣,化水而生的古典中国的县域样本。
2022年10月,松古灌溉区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,松阳的农耕文明汇入世界文明的大统而备受瞩目。
松阴溪从遂昌进入松阳的当口,有界首村,村口有禹王庙。上古传说,大禹治天下百川之水,而后才有田可耕,有粮可收。松阳人承继了中华民族古老的治水精神。
责任编辑 季亚娅 赵文广
(《十月.长篇小说》2024年4期 [5828])